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研究了中西方科技发展史后绘制了以下一张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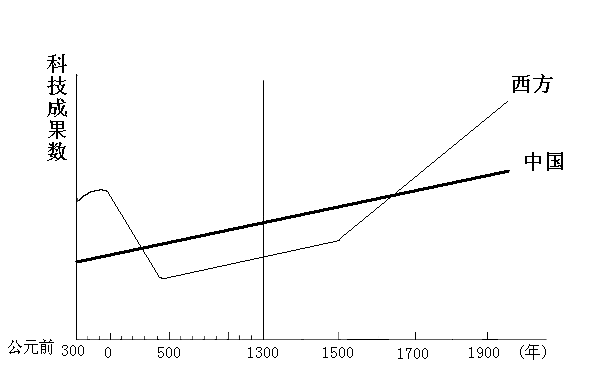
从思维方式的互补性看中医学与现代科学
李婷,陈晓东
摘 要:中医学与现代科学的矛盾冲突,根源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即非对象性思维与对象性思维的对立。这两种思维方式具有互补性,不可偏废,亦不可偏执。各尽其道,互为所用,庶几可得之。
关键词:思维方式;对象性思维;非对象性思维;意象性;互补性
几乎所有对中医学之科学性的批判都源自对于中医学与西方科学理论的比较,这里的“科学”,实际上指的就是现代西方的实证主义科学。这一批判始自西学东渐,并随着西方科学日益在我们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日益激烈。正当许多中医界的同道们为了中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力求使中医“科学化”、“客观化”时,我在不断地问自己:这种中国传统医学对于西方科学的不符合能说明什么呢?中医学的精神内涵是什么呢?中医一定要或者一定能走上一条以实验为基础的道路吗?我试图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及其发展历程中找到一些答案。
西学东渐之后,几乎所有中国古典文化的精髓都面临着与中医学同样的危机,这说明中国传统医学与西方科学之间的矛盾在深层次上即是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之根源在于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中西方人在认识世界时采取的视角和方法是不同的。
西方人惯用的是一种对象性的思维方式,即将整个世界(包括人自身在内)作为一种外在的对象进行研究,将认识的主体与客体截然分开,相互对立,这就是主体与客体的二元性。在认识的过程中,他们将对象进行分解、定义,形成概念,进而应用逻辑推理形成理论体系。这是一个由整体到局部再到整体的分析还原的过程,是对未知世界的间接把握。基于此模式的对象性思维过程,必然强调对物质世界的结构分析,其得到的理论体系必然是确定的、客观的、重实证的。这种理论体系必定是概念清晰而明确,推理严密而符合逻辑。因其研究的对象不同形成不同的学科,对人体的研究则形成西方医学。
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恰好相反,是一种非对象性的思维方式。中国人从未将人与自然万物分隔开来,天人合一是其根本思想。天地与我同心,万物与我并生的老庄哲学,反映在认识过程中就是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中国人是在有诸内必形诸外、由外而知内的理论前提下,通过直觉“领悟”
,从整体上把握事物。注重的是事物之间的联系,并且要求在认识过程中达到人心与道相合,即这种领悟过程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上与事物保持充分的一致性,对事物进行直接地把握。这使得其理论体系必然不是确定、客观的,也不是重实证的。
相对于西方科学,在非对象性思维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医学是一种意象性的理论体系。它明显地区别于西方科学,与西方哲学也难以融通。它不重视物质结构,它的概念并非通过解剖手段得来,故没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其所代表的意义是可变的、模糊的、抽象的。它的理论体系的形成也不是依靠逻辑推理,而是通过直觉领悟来对人与自然、人自身在不断的运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进行把握。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领悟之所得乃系难以言传,只可意会。然而,为了极不情愿的表达的需要,它多采用了意象性的比类的方式。
由上可知,对象性思维和非对象性思维是人类的两种互补的思维方式,而在其基础上分别形成的理论体系也具有互补性。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对中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它形成了中西方在语言、文学、艺术、建筑等方面的差异,并且这一影响一直贯穿了整个中西方文化发展史。在人类文明开始萌发的初期,当西方的哲学家兼科学家正企图将世界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来认识的时候,中国的哲人们则力求通过直觉领悟来贴近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以达到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这样,在古希腊形成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与之相对应产生了元气论。当西方古典文明之光被中世纪宗教神学淹没之时,中国也开始了魏晋时期的道教、佛教的形成与传播。由于西方思维方式对结构的强调,表现在神学方面即是人与神的绝对对立,神与人在本质上或结构上是不同的,要飞上天去,小天使就必须长上翅膀;而在中国,飞这一效果只需意会,无须长出翅膀即可羽化飞升。人即是神,神即是人,所谓“明心见性,立地成佛”,并有佛祖拈花示意的典故。这使得中国的宗教并没有象西方中世纪神学那样影响人类文明的进程。就在西方神学对科学大肆摧残之时,中国的冶金化学、农学、数术、天文学等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西方文艺复兴之后,人文主义代替了宗教神学,更强调了以人为中心、为主体对客观世界进行研究。这时对象性思维被发展到了极致,这个世界被分解,形成各种定义、概念,很快,一个庞大的西方科学体系就产生了。这一时期的中国,宋明理学的产生、王阳明的哲学使天人合一的思想深入人心。以前在寺院、道观中玄而又玄的东西被通俗化,所以更有影响力。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对象性思维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历史进程中,实在无法形成西方式的科学体系,更不会产生工业革命,中国的医学也不可能走上实证的道路。
这并不是说中国就没有产生对象性思维,只是没有得到发展。《庄子·天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1]
受此思想影响两千年的中国,当然就更重视个人修为而对物欲横流的世界形成一种自然的抵制。
两千年来,中西方人在各自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培育着各自的文明,一旦两种文明发生碰撞,巨大的矛盾便产生了。随着近代的西学东渐,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物质文明象西方的大炮一样震撼了中国,几乎有一举摧毁所有中国古典文化之势。中医学这一关乎人们生命安危的学问更是首当其冲。又由于西方科学的客观性、确定性,使人们更易理解和把握;而中医学的意象性、模糊性妨碍了人们的理解与掌握,使中医学在这场较量中更加处于劣势。当代,这种源自西方的现代文明几乎充斥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分子生物学、克隆技术、人类基因组计划……可谓将对象性思维发挥到了极致。如此诱人的繁荣景象,使得中医同道们不得不想到中医学的“科学化”、“客观化”。然而,中医学是建立在非对象性思维基础上的意象性理论体系,如果这一体系真的被“科学化”、“客观化”的话,那必然意味着这一体系的毁灭,取而代之的是西医学的理论体系。这岂不是与我们发展中医的初衷背道而驰?这是否能算中医学真正的危机呢?《庄子·应帝王》中有“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儵与忽时相与遇於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为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1]
对于中医学盲目地“科学化”、“客观化”,是否是在“日凿一窍”呢?
意味深长的是,当我们在为中国传统医学的前途扼腕之时,西方科学也面临着其自身的困境。早在古希腊时期,伊壁鸠鲁(Epicurus)就提出了著名的“二难推理”。他在给梅内苏斯(Meneceus)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和独立的,我们可以赞扬它或指责它。因此,为了保持我们的自由,保持对神的信仰比成为物理学家作命运的奴隶更好。前者给予我们通过预言和牺牲以赢得神的仁慈的希望;后者相反,它带来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必然性。”[2]
很显然,这一矛盾是由对象性思维引发的。事实上,西方科学对于客观性的过分强调,往往割裂了事物在时空上的联系和变化。它对世界的认识只是一个侧面,是不完全的,是假定研究对象在确定不变的情况下完成的,忽视了事物的变化性、历史性,在更广阔的时空上则表现出了其自身难以解决的矛盾。康德(Kant)、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海德格尔(Matin Heidegger)等都不得不在异化的科学与反科学的哲学之间作出痛苦的选择。而波普尔(Karl
Popper)和其他许多哲学家则指出:只要自然单纯由确定性科学所描述,我们就面临着无法解决的难题。现代科学的研究使这一矛盾日渐突出。不稳定性和涨落在从宇宙学到分子生物学的所有存在层次上产生的演化模式,非平衡过程物理学及不稳定系统的物理学表达使现代科学将与牛顿、爱因斯坦为我们描绘的那个无时间的确定性的世界告别。这一结果,将西方科学拉近了中国哲学。然而,为了描述这种非确定性,在对象性思维的基础上,伊利亚·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耗散结构理论创立者。)不得不求助于概率,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可确定的概率世界”里。这种表达仍让人有一种力不从心之感。这种在对象性思维基础上难以解决的矛盾,恰是非对象性思维基础上的意象性理论的专长。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和回避的事实是:在对象性思维为人类的物质文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它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甚至有些现代西方哲学家把人类不断扩张的物质文明比作地球上的恶性肿瘤。这几乎是其必然的发展规律,是隐藏于主客体的对立之中的必然结果。与之相反,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恰是非对象性思维所极力倡导的,这又一次证明了两种思维方式的互补性。
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研究了中西方科技发展史后绘制了以下一张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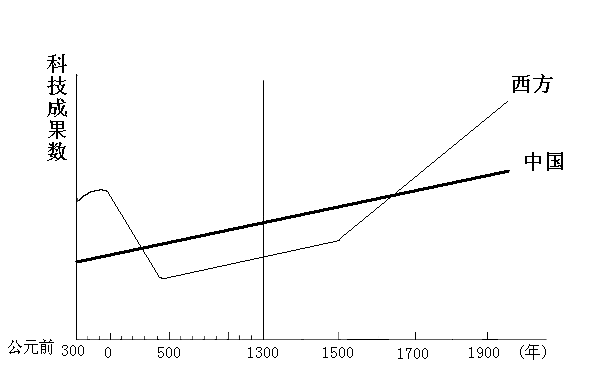
很显然,中世纪的黑暗使得西方在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任何科技上的建树”。[3] 谁又能保证在人类文明未来的发展历程中,由对象性思维所引发的现代科学的内在矛盾不会导致第二个“黑暗的中世纪”?谁能保证现代科学仍保持着文艺复兴后的发展势头?现代科学又怎样来消除其所带来的对人类生存空间的负面影响呢?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是否还有赖于非对象思维的参与呢?
在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中,百年、千年的时间只是短短的一瞬。无论是对象性思维方式还是非对象性思维方式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二者基础上形成的理论体系也都是人类文明的硕果。它们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任何以一种取代另一种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将二者机械地揉合也是不可能的。我不反对用西医的方法研究中医,然而,与其将中医西医化倒不如研究中医学更深层的精神内涵,按照其本身的规律发展中医。这一点似乎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更为重要,因为目前任何一个环节都不支持这种发展。正所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消灭了中医学的特色也就消灭了中医,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人类仍然需要非对象思维给我们以启迪,人类仍然需要意象性的理论给我们以智慧,人类仍然需要中医学作我们健康的向导。
参考文献:
[1] 李牧恒 ,郭道荣.自事其心——重读庄子.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96.第258、241页.
[2] J.Barnes,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London:Routledge,1989).
[3] 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沈阳.1986.第310页.
附注:此文发表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3月第2卷第1期。